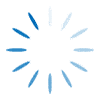就结婚这件事来说,二十岁的相月很难判定是否是一时冲动的产物,但又确实从没后悔过。
和张鹤厮混了一年有余,他突然郑重其事地说,想永远待在她身边。
她没有当真,这种你情我愿的玩乐关系怎么会长久呢?爱情,总是浅薄而缥缈,等她哪次在战场上待久了些,或是直接回不来,又谈什么永远呢?
于是她笑道,那你也要从军,不然聚少离多。
那时联邦和佐尔坦帝国的关系绷得随时要断掉。她嗅到了战争的前兆,也疑心自己要挂帅出征,便总纵容他,像将要远行很久不回来的主人在任由小狗讨亲亲抱抱。
张鹤便真的去了。新兵训练,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。
相月总是很忙,她偶尔闲下来纠结去不去看他,又觉得或许张鹤已倦了他们的关系。
自从荒芜星上捡到他,就一直养在自己身边。她是知道他本性里的凶的,这一部分也许并没有驯服,只是掩藏着;等进了部队可以靠武力生存,又何必来她这里出卖色相和肉体?
再次见到时,张鹤穿着统一制式的黑色军服,她差点认不出——说实话,见得最多的,还是他什么都不穿的样子。
他所属的部队在偏远的小行星上训练兼开荒。她是巡航时偶然路过,这条航线是内部公开且固定的,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张鹤知道她要来。却没有喊她的名字,只是盯得她后背都要起火。
相月本来在和驻军队长讲话,身边来来去去有人在运送物资,明明是很乱的背景,却一瞬福至心灵。回头便见他目光灼灼,她有些无奈地过去,打算抱抱他哄一下。
——她是不介意别人看着的,反正“相小将军养了个小白脸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
还有两步远的距离,她抬了胳膊就要抱他,已经看到他控制不住上扬的嘴角,乱糟糟的军帽也压不住的卷毛也快乐地翘起。他却又忽然看到什么,瞳孔骤紧,冲过来搂住她一百八十度转身。
她其实听到了,背后有很轻微的能量束破空的灼烧声,运输人员的厚底靴子特殊的落地声。她甚至猜到,大概又是无聊的佐尔坦的细作,想挑战联邦最年轻小将军的身手。
她想躲的,或是回身精准夺下再反杀,自己掏武器也能比那细作快。那一瞬间战斗惯性演练了无数种方案,但张鹤的动作是她始料未及。
等其他军官和士兵反应过来已经迟了。
张鹤被战友架着去找军医,细作也被很快按下带走审讯。相月站在原地,愣愣地看了好一会儿喷溅得满地的血迹。
他差点在她面前脑袋被烧个对穿。
那一地热烫的红,令她心颤。
第七军团的随行军医是全联邦最好的。其他人庆幸还好是相小将军碰巧巡航,不然这新兵的命要保不住了。
相月知道,如果不是自己在这,张鹤也无需遭此无妄之灾。
她坐在修复舱旁边看着,年轻俊朗的青年就浸泡在透明的液体里,紧闭着眼睛。
为了方便手术,那头漂亮的黑色卷发也剃掉了。相月还能想起它的触感,汗湿时是软的,像它的主人一样听话,只要拽住,就能听到性感好听的声音。
相月停留不了很久,干脆打了报告,直接把人带走了。
于是张鹤两天后醒来,就发现自己是在病号专用休息间——很眼熟,就是他被相月捡到的那天晚上住的那种。
原来是在第七军团的星舰上。
之前那些日子,大概她只是太忙了才没有来看他。看,现在他受伤了,她就将他带在身边了,她一定是喜欢他的。
一切仿佛旧日重现,晚上相月来看他,敲了门,又坐在他床边。
张鹤抱着她的腰,埋进她怀里,快乐得灵魂都在颤抖。
相月以为他在害怕,轻轻拍抚他的肩背,又低头仔细看了看他脑后的疤,“没事啦,伤口处理得很好,不喜欢的话就多泡泡修复液,不会留疤的。下次不要给我挡了哦,太危险了……”
她在关心他,在抱着他哄他,还说有下次,那就是还允许他亲近。张鹤几乎要克制不住嘴角,缓了几秒,才换上委屈的表情,抬头看她。
“姐姐……会对我负责吗?头发都没有了,不能让姐姐拽着骑我了。”
不到二十岁的相小将军听不得这种荤话,红着脸捂住了他的嘴,不知是不是慌不择言,“那结婚吧。”
张鹤愣了,她也愣了。
张鹤垂着眼,那高兴又忧伤的神色不知有几分是演技,“是为了补偿我吗?还是真心喜欢我呢?我是主人的狗,保护主人是应该的,不需要牺牲这么大来补偿我的。”
寻常人听了就要立刻表真心的茶言茶语,相月却认真思考了起来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张鹤心下一沉,就要挤眼泪补救,却突然被相月捧起脸亲了一下。
紧接着桃花眼里盈满笑意,比舷窗外路过的恒星还要明朗漂亮。
“是喜欢的。”
“不是因为补偿,也不是感动。只是突然发觉,是真的很喜欢你,不想失去你。”
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备战前夕兵荒马乱,结婚也一切从简。甚至没有像样的婚礼,没宴请什么宾客,只是飞快过完了结婚手续,在第七军团内部小小庆祝了一下。
许多军部内的长辈看到提交的报告,都试图劝她,也知她自小有主见,总是劝不动的。
长辈里,也只有周叔给她发祝福,说那是个好孩子,跟她很合适。
相月看到消息时,正在收拾张鹤。他瞒着她接受了第七军团那群人的“切磋”邀请,然后被揍得险些崩裂伤口。
什么好孩子,是不听话的小狗才对。
相月罚了不老实的部下加训。又按着刚泡完修复液的张鹤,命令他赤身裸体面朝墙壁跪着,站在他身后仔细看了看那道疤。
“就不想想身体还没好?也敢去跟他们切磋。”
张鹤老老实实答,“他们说,要跟你结婚就得和他们切磋。”
“就这么听话?之前不是心眼挺多的吗?”
年轻男人答得又乖又委屈,“我想和你结婚。”
“……伤口还疼吗?”
“有一点。”
相月小心地碰了碰伤疤周围的皮肤,都泛着新生的肉粉色,重新结痂的地方长长一道,看着有些可怖。
她的手指有些凉,贴在头皮上,激得张鹤浑身一抖,后颈竖起汗毛,前面也跟着勃起,龟头抵着墙壁。
相月的位置很容易瞥见,她故意将手指下滑,指尖掠过脖颈,肩胛骨,指腹顺着他的脊柱来回抚摸,看着他越来越硬。
“不然留着吧,让你长长记性。”
张鹤听话得要命,“好。”
相月又心软了。
明明是乖小狗,何必难为他呢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